原标题中国作协的德国联络站:黄凤祝博士的香江酒楼
作者:金弢
总编按: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之际,一批批文人作家相继走出国门,探寻外部的世界。在波恩(时为西德首都)莱茵河畔经营香江酒楼的黄凤祝博士,成为当代最早的中德文学交流的搭桥铺路人。他接待过无数的中国作家,并把众多的中国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 知青文学” 和 “改革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出版。刚刚从日耳曼文学专业毕业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的金弢先生,多次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后来他也来德留学并定居慕尼黑。30多年过去,当他回忆起当时中德文学交流的逸闻趣事,自然无法忘记黄凤祝博士曾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黄凤祝博士来自香港,后受聘中国同济大学任哲学教授,目前已经退休。
 位于莱茵河畔和波恩大学历史系大楼旁边的香江酒楼(Hong Kong)
位于莱茵河畔和波恩大学历史系大楼旁边的香江酒楼(Hong Kong)
今天,当年的香江酒楼已不复存在,这里盖起了新楼。年轻一代不再闻悉30多年前的往事。然而很多老一代留学生那时就经常在香江酒楼的露台上,放眼莱茵河,把酒谈时政。那个时代的中国,充满了朝气与希望。莘莘学子们视国事为己任,敢于指点江山,参政议政,褒贬时事。多年后的一天我故地重游,看莱茵河北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感叹不已。“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的名句不禁涌上心来。今日再读金弢先生如下的回忆文字,更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3月1日,就在此文最后的编辑过程中,我接到黄凤祝博士提供的多张照片,要不停地与他和金弢先生通信,辨认照片中的人物。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又不断地勾起我们陈年的回忆。我们尽力复原当时的人与事,让这一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历史留下一个不可或缺的篇章。
我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头尾加起来虽不到四整年,但正赶上1985 年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进入一个新阶段,外事工作非常繁忙,往往是第一个出访团的任务尚未完成,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出访团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签证要提前办理,这样仅有一本护照就不够用,为了工作,我拥有两本公务护照,到了1988 年因德方的私人奖学金,我在完成 “汉堡文化周”后为能以私人身份留在德国,事先特地去公安局又办了一本私人护照。这样,最后一次出访,我身怀三本有效护照来到德国。
中德文学家交流中绕不开的黄老板
在对德繁忙的外事交流中,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人物,他就是波恩“香江酒楼”的黄凤祝老板。第一次的接触似乎偶然,我们16人的作家团,加上我驻波恩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就读波恩大学的我国留学生地陪,共30来人被黄老板邀请在他饭店用餐,加上一些外宾,他宽敞的包间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因忙于翻译应酬,具体行政事物由秘书承担,所以整个过程也不知道哪位是老板。那顿饭是黄老板请的客,是事后才听说的。
 黄凤祝博士(左)与女作家遇罗锦(右)在香江酒楼的书房
黄凤祝博士(左)与女作家遇罗锦(右)在香江酒楼的书房

中国著名作家从维熙(左二)和来自台湾当时在柏林自由大学教书的车慧文博士(左三)与德国友人在香江酒楼的阳台上
知道他是老板是在全团都已上了车,汽车开始发动,他身着一件退了色的牛仔上衣,手提两个大塑料袋冲上车来。我因工作需要坐在头排,汽车快要走了,他没有时间多说话,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告别话,把两大口袋的东西塞给我,让我分给大家。我一看均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 CD,足足有五、六十盘,和鼓鼓的一大口袋巧克力。这两样东西,对当时为节省外汇、回国舍不得花西德马克买礼物的作家们来说,恰如雪里送炭。大家只顾着高兴,也没更多地去想这位黄老板怎么如此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自那次以后,往下几年的来德作家团都跟黄老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老板跟我们打交道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每个团的行程,他不知从何渠道得到消息,每次我们到达下榻的旅馆,他已迎候在位,并给每人准备了见面礼。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跟我们约定去他饭店吃饭的时间。作家们都很好奇,向我打听此为何人,我开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知道他不是咱们的使馆人员,虽是餐厅老板,但每次用完餐都不肯收钱。后来才知道他是位痴迷中国文化的爱国华侨。
 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馆文化处二秘孙书柱(《走不出的咖啡馆》一书作者)与著名女作家张洁在香江酒楼。1981年出版的张洁描写中国改革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翻译成德文出版后,一代德国人是通过她的小说了解中国现实的
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馆文化处二秘孙书柱(《走不出的咖啡馆》一书作者)与著名女作家张洁在香江酒楼。1981年出版的张洁描写中国改革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翻译成德文出版后,一代德国人是通过她的小说了解中国现实的
黄老板的事业原则是以商养文。他经营酒楼,把挣来的钱都投资在文化事业上:他办文学杂志、开书店、有雅知出版社、搞印刷厂,还亲力亲为,迻译中国古代及当代作家的作品,出了一系列装帧漂亮、文字优美的书籍,是 80 年代最早一批把中国文学译介到了欧洲,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向德国乃至欧洲搭建了最初的文化桥梁的人,写下了新时期我国文学 “走出去” 方针政策功不可没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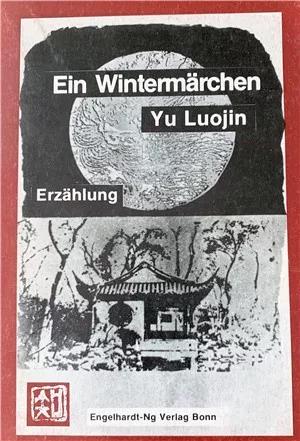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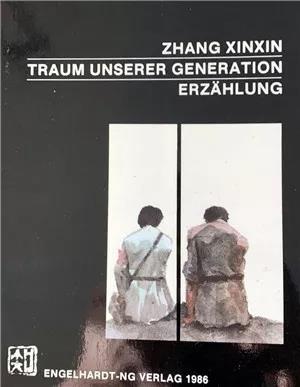
黄凤祝博士的雅知出版社(Engelhardt-NG Verlag)出版的书籍。左起:刘晓庆的《我的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与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黄老板经营餐馆是以商养文
黄老板为人谦谦有礼,从不夸夸其谈,是个绝对的务实派。工作废寝忘食,言而有信,极其讲效率。他为人低调,凡事不求回报,跟中国文化人建立了一面倾斜的落差关系。他对人的无私资助时常慷慨到让人费解。甭说作家团到了波恩他必定上门邀请,那时波恩为西德首都,是中国大使馆所在地,大多团队出访都绕不开去使馆汇报工作,这样每个团一到波恩,就躲不开黄老板的盛情邀请。
不光如此,黄老板还对作家团追踪陪同,“王蒙团”、“王愿坚团”、“邓友梅团”的访问重点城市是汉堡,他撇下饭店前来汉堡参加我们的活动。分组活动当翻译,陪同作家还时时慷慨解囊。一个酒店的老板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不管,能做到这一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后来我自己做了老板,感受就更加深刻。看得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达到何等深挚的地步。更为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夫人安妮(Anne Engelhardt),一个当年德国的汉学姑娘,跟咱们又没有同根同族血缘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笃爱、对丈夫献身于推广中国文化事业的理解、辅助和支持,让人感慨不已;她跟黄先生一样,低调内秀,我跟她见过那么多回面,至今始终回想不起她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对所有的的中国作家来说,她一直是一个默不出声、从不抱怨、事事有求必应但从不抛头露脸的女东道主。她上下一身黑色,包括头发,更凸显她的内在秀美。
 黄凤祝博士的太太安妮(Anne Engelhardt,左)和李子云女士(《上海文学》原副主编)在酒楼的雅知出版社书房
黄凤祝博士的太太安妮(Anne Engelhardt,左)和李子云女士(《上海文学》原副主编)在酒楼的雅知出版社书房
黄老板不仅 “家有食客三千”,还不知劳累地进行采访、撰写报道、举办文学活动,搞作品朗诵会。为了不让年老的作家路途来回奔波,他把自己离酒楼不远的大房子让给作家们住,以方便来酒店用餐。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生都住进了他的房子。我是团里翻译,习惯随着玛拉团长住,而在整个出访期间莫言始终跟我合住一间,这样莫言也一起留住黄老板家里。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
黄老板非常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非常善解人意。西德马克是每个中国作家求之若渴的宝贝,谁都指望利用一生难得的一次出国机会,到德国能攒到足够的外汇回国圆了彩电梦。黄老板除了请作家吃喝免费、送礼,还送每人丰厚的零花钱。他谙悉作家们是有个性的人物,自尊心强、好面子,是不肯轻易伸手索取嗟来之食的,他就巧出名目,给大家发放采访费、版权费、作报告费,让人拿了钱心安理得。住在他家里还能免费打国际长途。那时往中国打电话多贵啊,电话亭里,投币 20 马克,讲话不到三分钟,全部吃光。全团 15人加上留学生司机、陪同近 20 人,有时招集大家开工作碰头会,我会一再提醒大家电话不能动,专门强调了昂贵的国际长话费,我怕看不住,几次向黄老板建议把电话锁了。出于脸面,他死活不肯,还提醒大家住宅有电话,想往中国打电话就拨0086的国际前拨号。我们在国内打惯了公家的电话,对用电话会觉得理所应当。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时,有个同学来德后一下子找不到住处,德中友协的德国朋友主动免费提供家里的房间,还包伙食,这个不自觉的留学生偷偷用房东的电话往国内打,麻烦了人家一个月、白吃白住不说,还打掉了人家一千多马克的电话费。黄老板说。家里来了外人,如果把电话锁起来,这表示对客人极大的不信任,是对人的侮辱。黄老板之所以不锁电话,他是对我们的尊敬。其实有没有人打过电话或打了多少电话,看一看电话机上的计数器就明白了。
1987年秋,我们有一个作家团访问奥地利,为配合访奥,社科院《世界文学》专门出了奥地利当代文学专辑,我翻译小说《猎兔》,在维也纳还见到了作者本人。我说小说风格很接近屠格涅夫,让他兴奋不已。作家团里有天津的航鹰。这次出国,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怀给了她一笔考察费,让她到了欧洲考察国况民情,顺访西德、比利时,因考察款到手的晚,没法事先安排。访奥后我要陪康濯、柳萌团及时回国,不能同行。但航鹰是第一次出国,“老农进城”,又是一个女的,维也纳过马路还要拉着手,把她独自一人扔去两个陌生的国家,让人放心不下。我设法联系德国朋友,这种本来就是我们份内的事,因为太唐突,人家帮不上忙,无奈之下,只好又求助了黄老板。
 大约在1993年时,舒昌善(北京三联书店编辑)、作家池莉、林玉良(医生)、中国使馆文化参赞李世隆、陈晓(三联编辑)在香江举办报告会。
大约在1993年时,舒昌善(北京三联书店编辑)、作家池莉、林玉良(医生)、中国使馆文化参赞李世隆、陈晓(三联编辑)在香江举办报告会。
作家们受惠黄老板心存感激,但这种感触唯我最切,因为别人是难得的一回,而我是每次都在场,这种长期有来无往的交道,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人情债很重。慢慢地,到了波恩请吃请喝还给钱,在作协成了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作家单独来访,黄老板还要负责接送、陪同、翻译,夜以继日,特别航鹰的事是我直接联系了黄老板,为了表示歉意和谢意,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通信话衷肠
凤祝:
Beijing, 06,06,1988
你好 !提笔如晤 !
航鹰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回来了,虽然她因急着赶火车回天津未能在京跟我见面,但回家后随即给我写了长信,信中谈了很多你的为人、热心照顾、精心安排。同时她也提到了你近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说真心话,我在从奥地利给你打电话之前是犹豫再三的,我确是生怕惊动打扰了你。我很了解你的待人,一旦朋友有困难,提出帮助,你是不会拒之门外的。所以在求你帮忙之前,我已向别人求援过,在不成功的的情况下,出于无奈,况且时间又紧迫,第二天我要随团返京,航鹰又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在维也纳两周的相处也很愉快,我不忍心将她独自撇下不管,最后又不得不麻烦你这位好友,事后我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在此,我除了代航鹰向你千万次地道谢外,我本人也非常衷心地感激你,你的仗义不必多言,但愿日后也有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机会。
在大陆作家群、文人中,对你的状况我大概还算比较了解的,别的不说,单是 1987 年,我们就有三批以上的作家打搅你。你的性格谦虚内向,不计较经济得失,你自己是永远不会表示个 “不” 字的,但作为我们是应该体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我,因每次去人我都亲眼目睹了。说实在的,我有时感到很惭愧,为自己,也为有些人。我身为中间人,有些事没把握好,没提醒,这该是我的不高明、不到之处。关于此事,我跟我妻子(她是中文系毕业的)长谈了一夜,我们的共感是,我们太失礼了。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酷爱文学,热爱咱们这个民族,重义忘利,你热心好客,有如当年的孟尝君,然而······大概在某些细节上应有些改变,否则将是得不偿失。我私下认为,以后我尽量为你提供一些作家的动态,包括出访欧洲、尤其去西德的人员,我不必让人知道你了解此事,你可根据你的兴趣安排,有选择地作出处理。即使是你想晤面的作家,我也不赞成你较长时间地接待,可在他们顺道波恩作一短暂停留,进行一次文学交谈即可,不然你会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如来者不拒,反而会影响你的事业。多结交些青年作家。
九、十月份的汉堡 “中国月”邀请的作家有邓友梅、张洁、王安忆、程乃珊、鲁彦周、刘索拉,我看来也得同行,对方提到了我。9 月 27 日到汉堡,至 10 月 4 日,然后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周。如果去汉堡。届时我会设法与你联系的。汉堡活动后,我留在德国,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5 日 Osnabrück 大学举行 Remarque 作品研讨会,作为这个 Gesellschaft 的 Mitglied,我已收到邀请。此后,从 10 月16 日起,慕尼黑市文化厅邀请我去四个月的 Studienaufenthalt。完后,或许还会有其他单位向我邀请。其间我们定会有见面的机会。我听航鹰说,你需要宣纸,她给你带去的量够吗?需要毛笔吗?这些东西又轻又好带,我诚心想帮你忙,你若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把我看作一个朋友,直率地告诉我,能有报答朋友情义的机会是莫大的快乐。
今年 10 月,荷兰一家出版社要举行古华《芙蓉镇》的发行仪式,邀请了古华、朱晓平( 男,34 岁,《桑树坪纪事》的作者,今年中篇小说头等奖获得者)和另一名青年女作家 (此人我还在物色)。此事是一名西德人跟我联系的,他是驻京的联合国开发署、荷兰、英国、西德代表,名叫 Walter A·,他说,三作家访荷后,还要安排顺访西德,10 月 16日赴荷,在荷 10 天,在德 10 天,届时我已在西德。
以上所说的仅是提供你选择的机会,不是,绝不是什么义务,你若没时间,完全可以忘掉,不要当作一种负担,我只想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我今年要出三本书,都是翻译小说,赴奥前刚译完 Patrick Süskind 的《香水》,由文联出版公司出。去慕尼黑的主要任务一则研究 Thomas Mann,二则搞翻译,下一个选题是 Alfred Andersch 的《Die Rote》长篇小说。搞翻译是个苦差事,每天弄到两、三点睡觉,但不弄自己又不肯,真是自讨苦吃。好了,今天说了那么多,占用了你很多时间,问夫人好,她象你一样,谦虚、内秀!
Mit herzlichen Grüßen verbleibt
Dein 金弢
 在香江酒楼的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拜访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贝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左起: 黄凤祝博士、作家朋友、金弢、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官员孙书柱、德国翻译家 Monika Motsch(钱钟书《围城》翻译者)、使馆文化处官员与一秘、作协外事秘书
在香江酒楼的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拜访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贝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左起: 黄凤祝博士、作家朋友、金弢、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官员孙书柱、德国翻译家 Monika Motsch(钱钟书《围城》翻译者)、使馆文化处官员与一秘、作协外事秘书
后来我求学到了德国,三次路经波恩都没敢去找他,就是怕又麻烦了他。黄老板后来放弃了酒楼,这位早年哲学、政治学博士受聘成了中国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直到前不久因关愚谦先生去世建立了一个悼念他的微信群,大家在微信上发消息时,不期邂逅,我们有幸又联系上了,时空相隔三十二年。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