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不可思议地回暖。二月的最后一天,我被迫搬离住了半年的杜塞尔多夫。疫情期间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英国变异病毒来势汹汹,让封锁了一整个冬天的德国三月解封的希望依然渺茫。谨以此文献给我在杜塞的六个月时光。
2014年我第一次来到德国,首站就在柏林呆了爽翻天的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居住多年的马德里,迎来了一位德国室友,正是来自杜塞尔多夫。室友人高马大,金发飘逸,真是可以用“俊美”来形容的男生,符合希特勒口中的“雅利安人”的一切特征。戴一块阿玛尼的手表,虽不是价值连城,但是和柏林人给我留下的鄙视名牌的印象还是大相径庭。
那时我还没去过杜塞尔多夫,只知道多夫(Dorf)在德语中是村子的意思。一个人口六十多万的地方在中国人眼中也就是个村落。我还问他那里通不通地铁,因为我判断城市和乡村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地铁:metropolis(大都会)这个词语的词根就是metro(地铁)。我问他:“将来毕业了,想不想去首都柏林找工作?”他不假思索地摇摇头。
那时的我怎么知道,德国可不像其它国家,把最好的资源全分配给首都。他说,他靠父亲的关系来马德里最有名的律所实习,将来回到杜塞也是默默接受父亲的安排。他还无奈透露,从中学就开始桃花不断。今天看来,他真是天生“凡尔赛”,也就是德国人对杜塞人的概括:hochnäsig(趾高气扬),和科隆的bodenständig(脚踏实地)形成鲜明对比。
2016年我在科隆呆了一个夏天,每周末都会去杜塞喝酒泡吧。去年搬到杜塞之后,又开始逢周末往科隆“蠢蠢欲动”。住在北威州的都知道,这两个城市似连体婴,好比足球界的皇马vs巴萨、时尚界的迪奥vs香奈尔、华尔街上的摩根vs高盛、手表界的百达翡丽vs江诗丹顿,明争暗斗,相爱相杀。
当年第一次去杜塞,刚到火车站就看到各色白领精英、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女士时尚潮牌加身,男士西装领带笔挺。和穿马球衫戴劳力士的慕尼黑、不论性别一人一件狼爪(Wolfskin)冲锋衣的汉诺威、头顶绿帽子骑自行车的柏林完全不一样。我也喜欢打领带,觉得很提升精气神,所以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德国这座为数不多的会穿衣的城市。
出了火车站就是日韩料理云集、中国餐馆扎堆的美食街,全德国的留德华都羡慕杜塞华人坐拥如此多珍馐美味。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著名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这里沿着运河两岸种植了栗子树(Kastanien),节日期间树梢点缀霓虹流光溢彩。奢侈品牌旗舰店应接不暇,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一派繁华景象。颜值本已不凡,衣品更添魅力,真是良辰佳景,美不胜收。
后来终于和金发室友在他家乡见面。被难民潮和恐怖袭击裹挟的德国已经不再岁月静好,我这位老朋友也不再“凡尔赛”。几年前的朝气蓬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年龄不符的沧桑。脸书上不再更新到处滑水冲浪的照片,而是张贴柏林的租房广告。他说他并没有按照父亲铺设好的轨道前进,而是选择了非政府组织。收入也肯定支付不起名牌。
寒暄叙旧过后难免谈到当下。我也问起这两年难民潮带给北威州的变化。他一方面承认短短的几年德国国运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又觉得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并说出了在我听起来依然“凡尔赛”的话:“(那些难民)我们不救,谁救?”他也许没意识到,这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和当年的纳粹不谋而合。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才会心怀“普渡众生”的信念,仿佛没了自己地球都转不起来。
北威州与荷比卢接壤,经济上迅猛强劲,文化上多元开放,是德国方方面面都名列前茅的联邦州。杜塞、科隆、波恩我差不多各居住过半年。眼见到大街小巷蒙头蒙脸的招摇过市,让人怀疑自己身处中世纪的阿拉伯还是21世纪的欧洲。耳听得杜塞的Oberbilk、波恩的Tannenbusch和科隆的Ebertplatz等街区都位列No go area,杜伊斯堡的Marxloh更是力拔头筹。
2014年北威州的乌珀塔尔街头出现“伊斯兰警察”。他们穿着印有shariah police字样的马甲,在酒吧、舞厅、赌场等场所门口劝阻穆斯林青年谨遵教法,不得入内,和也门、沙特等国的“道德警察”如出一辙。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马斯表态说执法是警方任务,不得借“警察”之名自行执法。
这只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萨拉菲教派在德国的一次集中体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统计全国共有五千多名萨拉菲分子,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生活在北威州。如此密集的程度和这里提倡的兼容并蓄是分不开的。只是敞开大门,进来的不只有阳光雨露,还有苍蝇蚊子,甚至豺狼虎豹。无论如何,和多姿多彩的杜塞的亲密接触暂时告一段落,我在“历久弥新”的科隆又会写下怎样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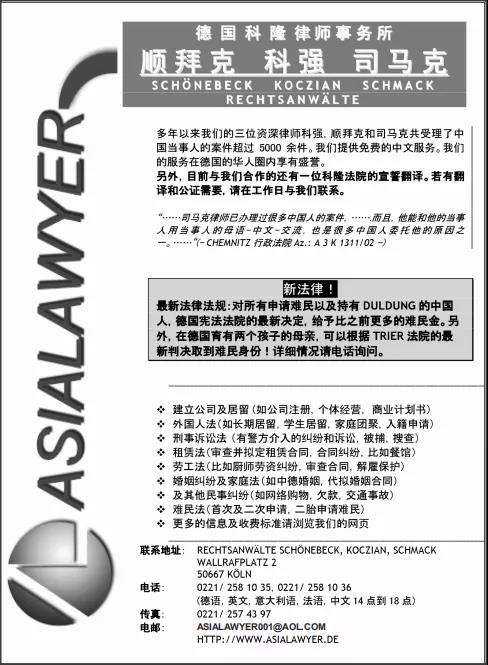 广告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11月06日)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莱茵河畔两颗璀璨的珍珠。科隆历史悠久,杜塞时尚新潮。两个城市间的敌对关系也是远近闻名。视科隆为第二故乡的专栏作者张丹红曾经在杜塞居住两年,对两市间的水火不容有切身体验。
广告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11月06日)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莱茵河畔两颗璀璨的珍珠。科隆历史悠久,杜塞时尚新潮。两个城市间的敌对关系也是远近闻名。视科隆为第二故乡的专栏作者张丹红曾经在杜塞居住两年,对两市间的水火不容有切身体验。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当时,我的工作地点德国之声总部还在科隆,我与在杜塞的男友搬到一起,每天在两市之间奔波。对科隆的旧情难舍,每天早上在高速路上远远看到大教堂,心里都忍不住地激动。科隆的朋友曾告诉我:”杜塞最美的地方是通往科隆的高速路。”但这显然不适于拥有杜塞牌照的人们 – 科隆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并道。
对他们来说,我现在是个变节分子;而在杜塞尔多夫,我像是个笨拙的间谍,不断暴露身份。比如在酒馆里,我经常习惯性地点科隆啤酒,引来跑堂恶狠狠的目光。假如我是男性,又假如我是典型的德国长相,那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看杜塞观狂欢节的花车游行,我一不留神就会喊出科隆的狂欢口号”Alaaf”,它富有韵律感,又琅琅上口,不像杜塞的”Helau”- 中间凹进去,像是坑洼的道路。
说起道路,一到杜塞市中心我就转向。于是买了一台导航器。但我个蠢东西带我在市里兜圈子。一位杜塞友人充满鄙夷地说:”这有什么奇怪。谁让你在科隆买导航?”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那座日本人聚居的城市里,经常有日本人用日语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一个流传科隆的笑话:一位游客在杜塞拦住一名科隆人问路:”您看着像本地人。请问我怎么能尽快到医院?”科隆人回答:”你只需要再说一次我是杜塞人。”
看来迁居杜塞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周末我照样回到科隆采购,看电影,间或去一家酒馆重温科隆啤酒的芬芳。每当在城里遇到科隆的朋友,他们都会充满同情或幸灾乐祸地问一句:”在禁城的生活怎么样啊?”
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而是北威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不过我还是禁不住想起我的家乡北京和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相互轻视。在北京人看来,上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又缺乏文化底蕴;男人怕老婆、抠门儿、没有幽默感;过去,上海是殖民者的天堂,今天,上海虽然富裕,但还得将大把税收上供给北京。上海人对北京也是怎么都看不上眼:首都人民不知新潮和生活品味为何物,只知道模仿上海;他们还把幽默和耍贫嘴混为一谈;再说首都有什么了不起,北京的首都地位还不是蒙古人和满人确立的?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当时,我的工作地点德国之声总部还在科隆,我与在杜塞的男友搬到一起,每天在两市之间奔波。对科隆的旧情难舍,每天早上在高速路上远远看到大教堂,心里都忍不住地激动。科隆的朋友曾告诉我:”杜塞最美的地方是通往科隆的高速路。”但这显然不适于拥有杜塞牌照的人们 – 科隆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并道。
对他们来说,我现在是个变节分子;而在杜塞尔多夫,我像是个笨拙的间谍,不断暴露身份。比如在酒馆里,我经常习惯性地点科隆啤酒,引来跑堂恶狠狠的目光。假如我是男性,又假如我是典型的德国长相,那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看杜塞观狂欢节的花车游行,我一不留神就会喊出科隆的狂欢口号”Alaaf”,它富有韵律感,又琅琅上口,不像杜塞的”Helau”- 中间凹进去,像是坑洼的道路。
说起道路,一到杜塞市中心我就转向。于是买了一台导航器。但我个蠢东西带我在市里兜圈子。一位杜塞友人充满鄙夷地说:”这有什么奇怪。谁让你在科隆买导航?”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那座日本人聚居的城市里,经常有日本人用日语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一个流传科隆的笑话:一位游客在杜塞拦住一名科隆人问路:”您看着像本地人。请问我怎么能尽快到医院?”科隆人回答:”你只需要再说一次我是杜塞人。”
看来迁居杜塞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周末我照样回到科隆采购,看电影,间或去一家酒馆重温科隆啤酒的芬芳。每当在城里遇到科隆的朋友,他们都会充满同情或幸灾乐祸地问一句:”在禁城的生活怎么样啊?”
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而是北威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不过我还是禁不住想起我的家乡北京和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相互轻视。在北京人看来,上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又缺乏文化底蕴;男人怕老婆、抠门儿、没有幽默感;过去,上海是殖民者的天堂,今天,上海虽然富裕,但还得将大把税收上供给北京。上海人对北京也是怎么都看不上眼:首都人民不知新潮和生活品味为何物,只知道模仿上海;他们还把幽默和耍贫嘴混为一谈;再说首都有什么了不起,北京的首都地位还不是蒙古人和满人确立的?
 本文作者张丹红
本文作者张丹红
北京和上海之间相隔上千公里,再加上南方与北方人之间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各异,因此,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科隆和杜塞同在莱茵河下游,相距40公里,两市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
在调查过程中,我甚至找到了两市结仇的具体日期:1288年6月5日。那天上午,两支上万人的骑士大军在科隆与杜塞之间的沃林根摆好阵势,决一死战:一方由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指挥;一方由杜塞伯爵冯-贝格统帅。初夏骄阳似火,身着锁子甲的骑士们汗流如雨。很快,两军阵势便被打乱。由农民组成的步兵见骑马的就杀,根本分不出敌友。沃林根战役的死亡将士达6000人,是中世纪最血腥的一场战斗。结果,冯-贝格伯爵战胜科隆大主教,杜塞从此扬眉吐气,获得城市权。由于两军分别与荷兰和比利时的贵族结盟,因此,沃林根战役在欧洲层面上导致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独立。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
不过,能说科隆和杜塞从此结下冤仇吗?恐怕不能。因为科隆大主教倚仗的主要是雇佣军。科隆市民早就厌倦了这位大主教,在沃林根战役中坚定地站在了冯-贝格伯爵一边。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原因,那么科隆与杜塞生隙可以追溯到1815年。那时,杜塞被确定为普鲁士莱茵省的首府。科隆大不服气。1946年,英国占领当局将莱茵地区和韦斯特法伦地区合并为北莱茵-韦斯特法伦州,首府又选中了杜塞。原因很简单:科隆除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其余基本在盟军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相比之下,杜塞的基础设施还能将就使用。
不过,这个决定给二战后两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杜塞成为时尚和经济中心,拥有自己的股市。30家达克斯最大上市企业中,有三家设址杜塞尔多夫。人口只有60万的杜塞每年税收远远超过百万人口的科隆。这些差别不禁又让人联想起北京和上海。
回到我个人:因为一到德国就选中了科隆,因此在杜塞怎么都不习惯。两年后,当我告别男友和整洁的杜塞,重新搬回脏乱差的科隆,心里那份舒畅就别提了。到了狂欢节,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挤兑杜塞人的笑话。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本文版权属于德国《华商报》,转载需与报编辑部联系,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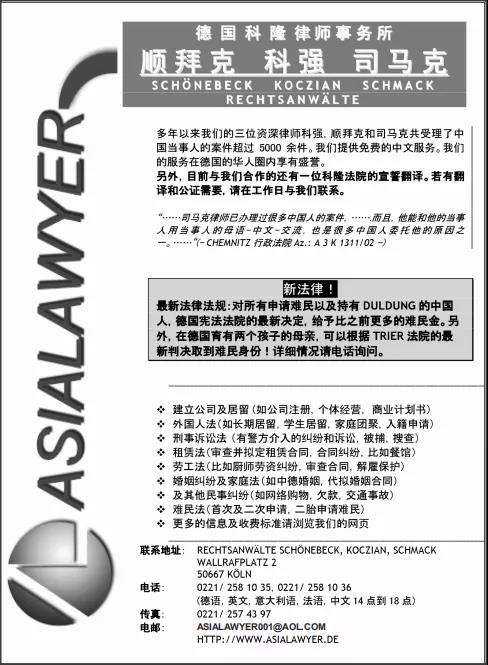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本文作者张丹红
本文作者张丹红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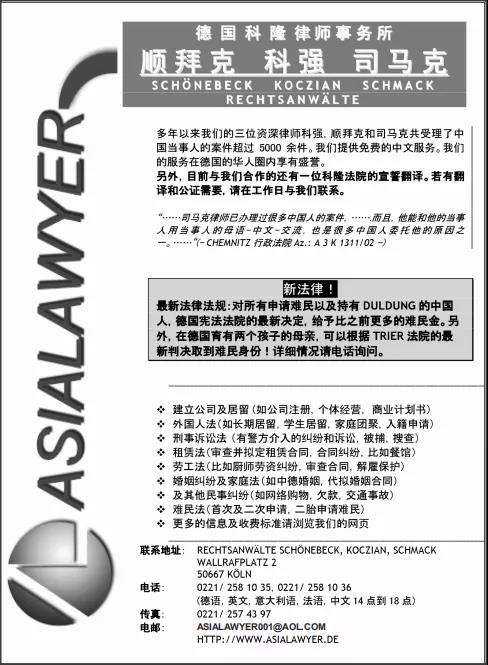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本文作者张丹红
本文作者张丹红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