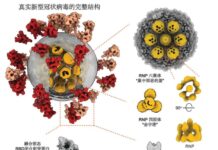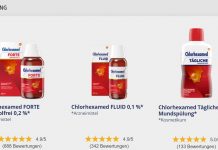2021年1月6日,发生了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事件,脸书于次日表示将封禁特朗普社交账号至1月20日他任期结束;8日,推特声明:出于对特朗普煽动暴力的担心,永久停用其账号。

禁言行为违背了言论自由原则?
紧接着,油管、被特朗普政府打压的抖音,以及苹果、谷歌、亚马逊等超过十五家社交网络平台和互联网公司先后加入封禁或限制特朗普发声的行列。
最新的性质相同的发展是,企鹅兰登书屋、阿谢特图书集团、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等多家美国出版机构的代理商和编辑联合倡议拒绝出版特朗普及其同僚的作品。
私营机构集体噤声,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同时禁了他数万支持者的账号,而他的背后还站着7000多万支持他的选民,数字大鳄们一次史诗级的言论大封杀,中国和世界为之诧异,质疑和批评之声四起。
一家海外华人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说:“这是最讽刺的一幕,一直倡导言论自由的美国,却剥夺了自己国家总统的言论自由。”一位在政治倾向上显然与环球网相左的评论者写道,“你们竟然还是以法律的名义,主张推特删号不是侵犯言论自由。在这些人谈及法律的时候,真是在侮辱和践踏法律的真正精神和尊严!”
在国际上,一些政治倾向不同的政商名流也纷纷提出批评,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财长勒梅尔和数字部长塞德里克·奥、法国极左政治人物梅朗雄和极右的勒庞,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政要、全球首富马斯克等。他们的批评焦点同样相对集中:推特等的禁言行为是否于法有据。
中国舆论批评的焦点是,特朗普被禁言是否表明他作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欧美舆论关注的焦点则是与事件相关的法律空白。从报道看,在提出批评的西方政商要人中,没人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事;早在去年6月和8月,推特和脸书曾先后对特朗普竞选团队采取过禁言措施,半年多来一众人等被封号,似乎也没有当事人援引第一修正案提出诉讼。
或许,无需什么政治学和法学的专业训练,仅在西方政体下的生活经验就使他们知道:推特的封号行为是公民在限制政府的言论,不是政府限制公民的言论,而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政府限制公民言论的情形才适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在中国许多批评家看来,颜色就是颜色,没有黑白之分,既然都是禁言,就是一码事。
在社会生活中,对言论的限制,概言之,有三种基本情形:
谈论噤声特朗普是否侵犯了其言论自由的问题,决不能像环球社评那样“无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什么”,相反,必须从该修正案的原文出发。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是:“国会不得制定下述法律:拥立某种教规或禁止信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限制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和平地呼吁政府回应诉求的自由权利。”
与言论自由相关的宪法条款还应当包括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表述。第五修正案申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表述中没有言论自由的字眼,但条款中的“自由”当然是包括言论自由的——在1925年“吉特洛诉纽约州案”的审理中,最高法院判定,作为针对各州的第十四修正案,其自由保护条款包含了第一修正案的立法宗旨。
如果说第一修正案是关于立法的规定,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表达则是划定司法红线。从三条修正案的行文看,都是国会自我设限和对司法的设限,并未涉及行政权。但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施政,国会就保障言论自由为立法设限,也就从根基上排除了行政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可能。
显然,美国宪法第一、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规范的,仅仅是国家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公法关系,其立法主旨是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府压制公民自由。而脸书、推特等是私营机构,它们噤声特朗普,也是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但与美国宪法所规范的情形正好相反,这里是公民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款在这里断无适用之处。
在被推特等封号时,特朗普兼具美国总统和美国公民双重身份,实施限制行为的是私营机构,这恰好对应着言论限制的另外两种情形,即公民限制政府的言论和公民相互之间的言论限制。先看公民限制政府言论的情形。
死抠法条字眼,推特等的封号行为与美国宪法言论自由相关条款没有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从评论者所谓“法律的真正精神和尊严”的角度看,推特等的封号行为恰好符合美国宪法精神以及美国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相关判例。
美国宪法精神一言以蔽之:限制政府权力
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被称为公民自由权利法案。不过,从行文措辞看,称之为“国家权力限制法案”更为恰当。这一点,不需细看便一目了然。十条权利法案,有八条明言政府“不得如何如何”。
其实,宪法修正案全部二十七条中的其他十七条,同样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宗旨的。十七条中除了其中的四条,有九条使用了政府“不得如何”的措辞,另外四条虽无“不得”字眼,但“不发生效力”“不发生影响”“必须”等措辞,所表达的依然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推特等对特朗普总统禁言,符合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精神。
除了宪法,国会其他相关立法及法院的相关判例,更直接、更具体、更清晰地彰显出在言论自由方面对政府的限制。
所谓言论自由,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公民就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自由传递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不同的著述对该定义在措辞上或有差异,但有两个要素是确定的:
(1)权利主体。公民是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主体。有一类特殊公民,即政府官员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是否与普通公民一样平等地享有此权利,这个定义没有说。但稍后我们会看到,较之普通公民,美国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论自由受到更多限制——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的附加约束,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题中应有之义。
(2)权利内容。公民的言论自由限定于议论“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逻辑上说,言论内容超出这个界限,涉及私人事务,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由此可知,诸如不得借口言论自由对他人进行诽谤、不得以言语对他人进行威胁云云,概属无稽之谈;言论自由的规定原本就是把私人或私人之间的事务排除在外的。
然而,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没有绝对分野。特别是,政治人物的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之间几乎没有界限。正因如此,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私人事务的批评,通常也会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美式言论自由”中,政府及其官员与普通公民之间是不平等的,前者是弱势群体。
较之普通公民,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在言论自由权利上的弱势地位,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当年4月1日《环球时报》就此发表评论认为,美国的言论自由“挂了”,是“冒牌货”,显示了美国政治的“小气”。此番议论表明,资深媒体人胡总编对言论自由的市场状况完全懵懂;他不知道,这里一直是冒牌与正品混杂,只不过消费群体不同。在有的体制下,政府常受冒牌之困,它必须谨语慎言,而民众则尽享正品之利,几乎出言无忌;有的体制下情形正相反,政府说什么都行,民众公开发言则要瞻前顾后。
胡总编嘲笑的美式“冒牌货”属于前一类——充分的自由只属于大众,政府则一直被法律“挂着”。换个胡总编更易理解的表达吧:比方说,普通公民汤姆赞扬苏俄革命,意见与之相左的议员或任何其他人只能与之争论;政府官员汤姆赞扬苏俄革命,议员或其他公众有权要求他闭嘴。不过,胡总编的“小气”一词很可取。确实,在向政府授权方面,美国政治确实显得小气。
特朗普的推特写作是公务行为,不管他说了什么,不管他说的是否属实,也不管他说的话是否关乎公共利益,像塞巴罗斯一样,被禁言的他无法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使自己获得司法救济。不知特朗普及其被禁言的同僚是否知道这类判例,无论如何,他们的律师团队对此应该非常熟悉。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已被社交平台禁言多日,他们至今没有援引宪法相关条款提起司法诉讼。
推特等社交平台对特朗普封号,是公民社会限制政府权力的最生动示例。
从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看,特朗普被私营媒体禁言是否意味着其宪法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呢?
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除了法律明确禁止的言论,还有无数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情形:家长与未成年子女、老师与学生、老板与员工、主管与下属、主持人与嘉宾及听众、出版机构与作者,等等,限制言论的情形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着。
音乐厅里高声说话被制止,作品被出版商拒绝,广播电视台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民主党造势的场子肯定拒绝共和党人登台演说……等等,所有这些“民间”限制言论的情形,都与宪法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权利没有关系,被限制、被拒绝的人会感觉不爽,但只要不是糊涂虫,没有当事人会想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受到侵犯。
推特、脸书等企业与特朗普公民之间是关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封号行为与其他“民间的”限制言论的情形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再扩大点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后,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撤销了30多年前授予特朗普的荣誉学位,美国职业高尔夫锦标赛声明把2022年冠军赛事移出特朗普高尔夫球场,德意志银行停止与特朗普公司的业务往来,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等银行暂停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等,这些都是另类形式的“禁言”。
推特等媒体平台对特朗普封号,与上述私营机构与特朗普的“断交”,性质完全相同。银行等企业的行为有可能侵犯特朗普合法的经济利益。同样,如果特朗普认为“粉丝”资源是他的财产,那么,推特等的封号行为有可能侵犯宪法赋予他的财产权利,但这与他的宪法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权利风马牛不相及。
从限制言论的三种基本情形看,推特等对特朗普封号,或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适用的情形相反,或在精神上与宪法一致并符合相关司法判例,或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无关,但在任何情形下,都没有侵犯特朗普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当然,没有侵犯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决不意味着推特等的行为从其他角度看也是正当的,决不意味着它们的行为没有问题。比如,巨型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虽然可能与宪法无关或没有违宪,但仍有可能违反其他法律,比如违反“反垄断法”并因此而受到制裁。
推特等社交平台的禁言行为有问题,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前面说,推特等噤声特朗普,与其他私营机构与特朗普的“断交”,两者性质完全相同。这里要补充说,从民事主体关系的角度看,性质相同,但从事件规模及其深远后果的角度看,两者却可能是天壤之别。
企业巨头与中小企业以及消费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但为了防止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及其他垄断行为,必须依法约束之。然而,无论怎样,提供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巨型企业所能侵害的,主要限于市场上其他参与者的经济利益。
网络媒体巨头们则不同,它们做的是“言论”生意,如果任由强可敌国的网络公司封杀它们不赞同的言论,并且这种封杀举措并无法律依据,而是遵循公司自立的规则自行其是,这有可能在政府之外,发展出另一个压制公众言论的机制,从而整体上对国家政体造成影响,因而更有必要依法约束使之不得妄为。
针对噤声特朗普事件,欧洲的政治家们没有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事,而是几乎一致地认为应有新的立法以应对信息巨头的行为,应当说这是对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之道的准确把握。或许,欧盟拟议中监管数字平台的《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的立法进程会因这一事件而获得新的推动。
自约翰·弥尔顿在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年代发表“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以来,社会大众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已将近四个世纪,斗争的指向也都是要求把大众就政治和社会事务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国家权力的管束下解放出来;相关的立法和司法、严肃的政治学和法学著述也都是从国家权力与公民之关系的角度审视言论自由问题的。
私营公司噤声一个大国总统,瞬间在政治人物与其千百万支持者之间竖起屏障,这一突发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坐标——信息时代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原本属于公民之间言论限制的私人问题成为了公共问题。如果由此开启相关的立法进程,关于言论自由的立法将从公法范畴进入到昔日的私法领域,人类法制史有可能增加新的篇章。
2021年1月29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