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性质原因,偶尔得以打入杜塞尔多夫抗疫大后方——市健康局,做了回卧底,片面了解行政后台运作,间接平复一下德国华人那不平稳的心。
2020年3月,不顾疫情全球蔓延,德国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一年一度轰轰烈烈的嘉年华庆祝活动。相关报道请看《新冠病毒蚕食德国:一天猛增19病例 起动应急机制 德国成传染源地 失控已难避免》(点击阅读)。
对于北威州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民来说,这嘉年华是每年的高光时刻,号称年度第五季。在一个嘉年华筹备集会上,毫无悬念地,多人感染并造成爆发,小城成了疫区,被紧急封锁。
相比国内的严阵以待,封锁到住户小区,只能说德国的封锁,在我们华人眼里,处处都是筛子。
绝大多数德国人该干啥干啥,上班的继续上班,上学的继续上学。大多数感染者还都无症状,只有极少数有基础病的进了医院。这导致一时间新冠病毒是“流感”的言论甚嚣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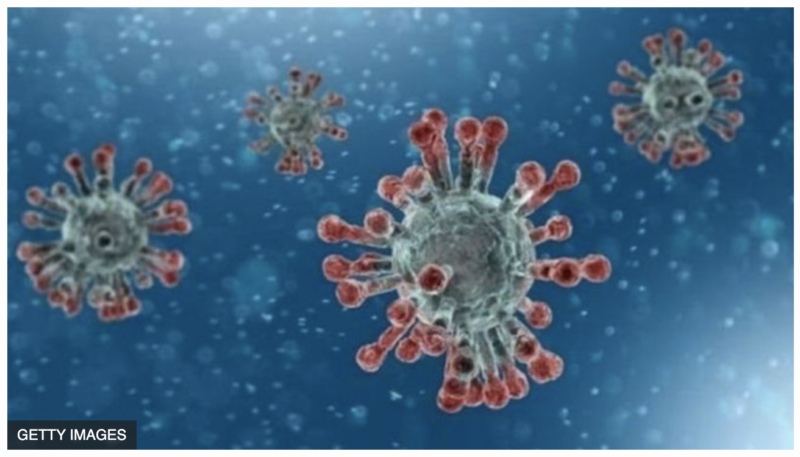
直到意大利那边儿呼吸机开始不够用,德国人才开始统计医院可用呼吸机和可用床位的数量,脑回路不可谓不清奇。口罩是早就被咱们都寄回国了,手纸一时间成奇货可居。相关报道《德国新冠囤货厕纸第一,能当钱花还能吃,打架坐牢为厕纸,还有一个“厕纸首都”》(点击阅读)。
医院都没口罩了,德国居然还从法、意进口了几个重症患者。大街上戴口罩的居然只有华人,更有因为戴口罩被赶下车的奇葩事儿,深有风雨欲来之感。相关报道《以大爱迎战新冠:72岁老人为让年轻人活下去而选择死亡,德国救治多位法、意重症病患》(点击阅读)。
当医院里可用呼吸机越来越少,几近临界时,德国“钟南山”的声音终于盖过所有轻视疫情严重性,反对强硬抗疫情措施的外行人声音。毕竟他们也曾经笑话过天朝防疫措施之“笨拙“,甚至以中国强硬封锁政策攻击过所谓人权问题。
可是,但是,可但是,热爱统计相信数据的德国人突然惊讶发现,医院空闲床位越来越少,医护人员越来越不够用,本来就难约的医生更是再也约不到了。于是,经过各州在议会里无休无止艰苦卓绝的讨论,第一波松散封锁终于来了。

在咱们了解过国内严防死守的人看来,那一波封锁就…稀松。不过其实后面几波封锁也没严格到那儿去。
超市医院是照常可以去的,自己开车出去串个门也是没有人管的,感染者隔离是居家的,除了同一个公寓里一起住的人需要隔离外,其他接触者是照常上班的。
在封锁令颁布后某天,作为市政府所属下属企业,老板终于得到上级讨论许可,让我们开启居家办公模式。不管怎么说,居家办公还是很舒服的。除了担心一下哪天新冠变异成僵尸病毒,把杜(塞尔多夫)村变成寂静岭之外…就是继续进行社畜之搬砖运动,背景音是新闻里无休无止的对有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讨论。
某天,不用去办公室就节省了洗脸用水的我,嚼着早饭,打开电脑。因疫情停摆的单位每天很少有邮件来,所以当有邮件的提示音响起时,被惊出一身鸡皮疙瘩。
邮件是市健康局对所有城市下属单位工作人员的义工召集信,号召大家在八小时之外以及周末时间以义工(志愿者)的形式到健康局去接新冠热线。
要说这市健康局在疫情之前可算是个清水衙门,属于城市运作管理部门。由于医疗卫生保障系统还算完善,健康局除了日常监管,基本没有具体基层任务。
但是疫情来嘞,他们清闲的小日子也就到头啦。全局人仰马翻的同时,惊觉人手严重不够。各种抗疫措施的具体实施都需要人手。于是召集一切有生力量来救火。我收到的这封信是新冠热线接线员的召集令。
其实我回信响应号召的时候内心是犹豫的,觉着大概率不会让我去。我一母语不是德语的中国人,去接如此重要的新冠热线,人家会觉着我是瞎凑热闹去添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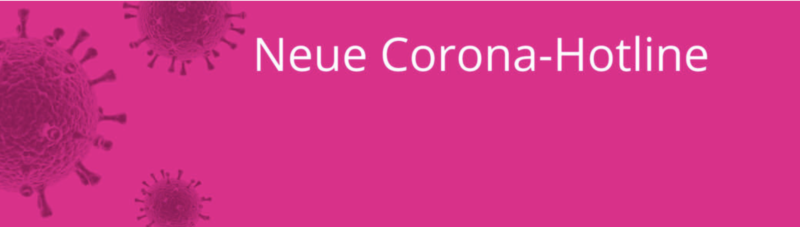
可是,三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模板确认信,咬文嚼字地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并要求下午四点去集合点报道。
顿时有当年被选上当少先队员的激动,心里却也犯嘀咕。在这居家办公自我隔离的日子里,外面疫情是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居然需要我一外国打工仔操着七分熟三分生的德语给市政府接热线?
下午四点,忐忐忑忑来到培训点,晚班负责人是健康局一个严肃大爷。一脸疲惫,眼袋快到腮帮子了。一边灌着咖啡,一边对我们这群从城市各个管理单位和下属单位,一脸懵逼,不知道要来干啥的小虾米表示感谢。
大爷是真累了,据说三天没回家了,一直坚守岗位,堪称杜赛“王进喜”。大爷先给我们普及新冠病毒知识。作为远程关注上半场的选手,我感觉我对新冠疫情的理论基础和大爷差不多,这几天听新闻把该知道的词汇也都学会了,顿时对这工作信心满满。
下一步就是培训我们的话术。按照大爷说法,咱们是代表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怎么着也得亲切可亲,同理共情,不卑不亢,专业笃定。用词要标准文雅,态度要热情诚恳,立场要坚决坚定……我刹那间又觉着这活儿我干不了了,羞愧地和大爷说,“我估计文雅不起来,德语大白话能说明白了就不错了。”
大爷早有准备,美(喜)滋滋拿出一叠A4纸,题目是《新冠热线接线标准流程》。
不愧是全民处女座的德国基层公务员,在这叠纸上不仅有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连各种表达方式都和德语教科书似的罗列其上。遇到什么情况给什么建议,遇到热线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要联系的相关单位及联系方式,通话记录格式,林林总总,十几页。看的我头昏眼花,这简直就是给我半小时学习时间学习一门新技能,然后就要上战场的节奏。
要么说我们中国人久经“考(和)验”呢,拿出上学时临阵抱佛脚的精神头儿,硬生生将“教科书”背下来,带着一脑门子的官司,我开始接电话。
第一通电话当然是紧张的语无伦次,放下电话我后脖颈子抽搐着疼,当年答辩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有点羞愧地和边上听的大爷道歉。大爷却说我表现不错,该说的都说了,信息给的准确,虽然有语病,但胜在态度好……态度好,这是新冠热线的重点吗?
大爷却说,其实现在资讯发达,绝大多数人早已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信息。可是信息太多,太杂,有时候良莠不一,很容易造成恐慌。
尤其是打电话过来的人要么是有症状怀疑自己感染了,要么是接触过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多多少少有心理压力,需要准确确定的答案,让心里有个情感依靠。
作为城市职能部门,给市民提供可靠准确信息,是市健康局的义务。新冠热线目前重要的职能是安抚社会情绪,防止不智的动荡。
好吧,电话那头的情绪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情绪被大爷安抚了,连大爷的眼袋都变可爱了。接下来的电话就越来越顺了,连第二虚拟式都能用上了。
这可是除了当年德语语法考试的时候用过,之后再也没用过的高档语法啊,我觉着我德语又上了一个台阶。

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安抚了两周市民情绪后,新冠热线得到新任务副本:给疑似感染者预约测试。
那会儿测试点还很少,测试工作人员也少,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和来电人的交谈,确定他是否急需测试。
这疑似标准就很难,发低烧算不算?烧到几度算?咳嗽算不算?一个小时咳嗽几声算?和患者有接触算,接触多久算?都是一个个的大问号。
然后慢慢的开始集体爆发,学校一个班里有一个孩子确诊,理论上所有孩子都得测,但是坐的离着挺远,平时相互看着不顺眼,没有接触,要不要测?楼下有人确诊,但是楼上发烧了,没记着有啥接触,但是共用地下室洗衣房,算不算疑似?
凡此种种,那会儿杜村测试能力太小,真的只够给非常疑似的人测试。很多想测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测。和现在一条街上三个测试点的盛况相比,简直两个世界。

就这样到了夏天,第一波疫情平复下去,我们单位复工。我又天天得穿的人五人六地去上班了。新冠热线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少,卫生局也新雇了全职雇员,他们自己人就够用了,就不用我们这种外来人员了。
我以为,下半场打完了,可以静待残余随风而逝了…那时的我忒天真。
2020年8月的某个周三,早晨昏头涨脑醒过来,浑身每个毛孔都痛。体温37度6,严重怀疑自己中招了。
立马回想都接触了谁。不得不很遗憾地承认,周一和单位所有领导都有过紧密接触。悲催的我觉着捅了马蜂窝。要是我们单位的领导都因我而感染新冠,估计得上热搜。题目我都想好了,北威州府某单位一中国雇员把所有管理层人员感染新冠,部门陷入工作停滞……。
打电话给新冠热线那个说了无数次的号码,预约核酸检测。接线小姐姐的标准接话术,让我一阵恍惚,两个月前我还坐在电话线另一头呢。
测试预约顺利,周五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上门来取样时,烧已经退了。
当天结果就出来了,还好是阴性。马上如临大赦通知单位负责人后,还是有点儿反思。我其实还是很小心的,没事儿基本不出门,感染上新冠病毒的概率非常很小。
但是当我告知热线,我曾经去单位与很多人有紧密接触时,并没有针对相关疑似感染病例紧密接触人的管理办法。

个人认为,如果我真的感染了,同事们真的是一个都逃不掉,全都得中招。从周三报备,到周五得到检测结果,若是确诊估计早就扩散了。
2020年夏天一过,疫情又起。
当时管理新冠热线的一个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人手又不够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和兴趣,继续去卫生局打电话。当时心中还是有点儿小窃喜,这说明我上一波接电话工作做得好,不是吗?

但这回给我的工作任务变了,不让我接电话了,而是打电话,通知确诊者居家隔离。
这不是个好差事。卫生局直接从分析实验室得到测试结果和病人全部信息,当我们打电话过去给确诊病人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确诊了。我们给他们三个坏消息:确诊了,要隔离,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
任务看起来简单,实际细节很多。
比如,新鲜出炉的《传染病预防法》规定,确诊后居家隔离,可是当时对没有确诊的疑似患者的行动没有限制。于是很多人其实在测试和确诊之间接触了很多人。我们就必须把所有接触人的信息都收集起来,然后一一通知居家隔离。
现在《传染病预防法》相关条例已经改了,从测试之日起,疑似患者必须居家隔离,直到获知分析结果。
再比如,已经作为感染者亲密接触人在隔离中的人,却确诊了,隔离日期怎么算。是按原有隔离日期算,还是以确诊日为起始日期开始重新计算?凡此种种都是重要的细节。
每天都有新的更新信息,每天都能得到新的任务。当然每天都能和奇葩的人通电话。大多数人还都是挺配合的,通知居家就居家隔离,毕竟健康局也是个局。可是,所谓瓜子嗑多了什么仁儿都能碰上,时不时就能碰到难搞的人。怀疑我们是诈骗电话的,口出不逊的,啥也不说的,满口谎言的。

来做义工打电话的好多都是年轻小姑娘,时不时就有打电话打的泪水涟涟的。给我们做心理建设的同事每天和我们说,咱们是代表城市管理的,通知隔离是有法律依据的,对方态度好,咱们就有礼可亲,对方态度不好,咱们就得强硬。八小时外来为人民服务,咱不能受气。
刚说完,我就打通了一个油盐不进的人的电话。我通知他确诊隔离后,他死活不口头同意自己隔离,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后来还说我是个骗子,拒绝给出接触人信息。我能惯着他?立即严肃重复一遍卫生局通知,挂电话后直接通知警察局。最后声音有些大,同屋同事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后来还有人试图安慰我,我虽然个头儿小,但是心脏大啊。立即表示,我很好,我没事,摊上大事儿的是电话那头那个人。
设身处地的想,这群借调的志愿者真的是富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很多都还是学生,在政府各部门接受培训,都是基层工作人员的储备力量。或者平时工作八小时后,傍晚再来这里为抗疫做贡献到晚上10点,或者牺牲周末来这边嘚吧嘚八个小时。
尽量态度温和与患者交流,抽丝剥茧追踪接触轨迹,通知到所有接触人。更别提那些接手去通知学校,一个班级所有孩子包括家长都要隔离的同事。
还有不说德语的,没留电话号码的,难民,居无定所的,吸毒者,问题儿童或者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每个感染者都是特例,没有工作模板可以套用。认认真真做这些事的人,除了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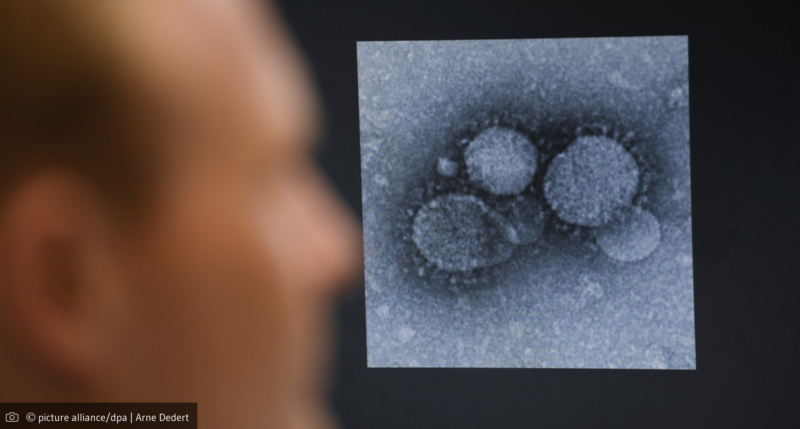
时不时,在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我们能清空当天任务时,负责人还会来夸奖一下我们勤奋工作,语气充满自豪,虽然小矫情,但是我这个在这大后方卧底的中国人,也与有荣焉地时不时小激动一下。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每周至少去做一次这种工作。
随着疫情起起伏伏,时不时每周三四次去加班。现在很多健康局的人都认识我了,开玩笑问我要不要转去健康局工作。我和他们表示坚决不去,还是工程师工作适合我。和标准以及数据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容易多了。
疫情最近似乎又有反复,下个月的班已经给我们排好了。和我一起打电话的同事已经换过一拨人了。
但我依旧坚挺在周末电话第一线,天天与追踪紧密接触人,或者搞清感染者行程这种拧巴事儿斗智斗勇。已经将近两年没休过假了。上回这么任劳任怨的做一件事儿还是在学生时期写论文做实验期间。
我有幸参与的仅仅是德国所有抗疫工作中微小的一环,但是为了组织这小小的一环,管理层面需要考虑到雇员法、劳动保护法等各种法律要求。
比如德国雇员法规定,不允许在疫情缓解时解雇不再被需要的雇员,所以只能召集城市政府下属单位有长期工作合同的员工来救急。
再比如,劳动法规定必须保障雇员人身安全,所以所有消(毒)杀(菌)措施,工作环境,防疫保护物品发放,甚至疫苗接种措施都必须先期组织完善。
由于疫情发展和劳动保护法针对防疫的要求更改,我们曾经换过三个工作场所,从一开始二十人大厅,换到现在每两个人一个屋,充分保证社交距离。每换一次场所都涉及到电脑电话IP地址等一系列繁琐工作。背后组织者的投入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
工作方法一直在改进中。
从一开始的所有报告都用纸,到现在全部联网,数据库统一工作进程。在无纸办公这一潮流中起步稍晚的德国人用了六个月,大概分了三步,逐步实现过度。我觉着还是挺快挺靠谱的。而且,就防疫法每周更新的频率来看,号称欧洲第一古板的德国人,想快也是能快起来的。
工作内容也一直在随着疫情发展更新中。
最近添加的工作内容是对确认感染期期间乘飞机的患者的邻座和前后排实行追踪和通知隔离。还有比如接下来对国外度假归来人员的控制。
虽没参与国内战疫,但想来,哪里都是一样的,任何抗疫成果都是基层工作者聚沙成塔,任劳任怨成就的大道。国家和城市管理的职责之一就是保障民众安全。此次疫情中,国家城市管理能力的水平高下立判。
我吧,虽然一不小心撞上了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这一波倒霉事儿。但还蛮幸运可以打入“敌后”——在城市新冠热线工作。

作为外国人,我真实的体会到杜塞尔多夫,这个国际大农村的开放和包容。我能把这个工作做下来当然也有我的长处。
作为外国人,我可以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外国人的很多难处,有共情,有耐心,态度好,我认真负责,头脑清醒,我神经大条不纠结,我会三种语言,由于提早关注了国内疫情,我一开始对新冠的理论基础还超前了同时开始的同事。我还有一个开明的老板,他还挺支持我来做这个工作,甚至给我排过一回雷。
得对得起这份幸运,所以,接下来的每个周末,我接着去打电话。
转载需与本公众号联系,
并注明来源:微信公众号 “德欧华商”












